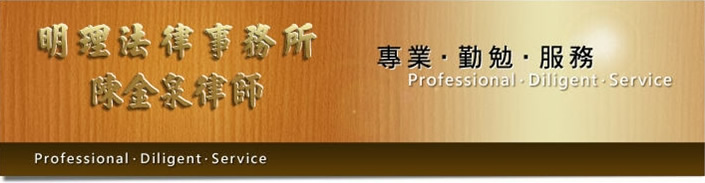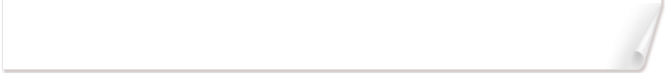2025.5.6網紅律師解僱女學習律師勞動法問題簡析
壹、前言
一、基本事實。
根據某律師臉書所載對話擷圖,女學習律師涉及勞動法議題的該段陳述為:「我實習那年因為不拿掉小孩被(雇主)fire以後,後面肚子大就找不到工作了,領失業給...」(註一)
二、討論範圍。
本文謹以上述女律師自述文字之內容,簡略分析其涉及的勞動法「解僱」議題。至於其他可能涉及的律師倫理、道德,甚至是非對錯、內容真假等問題均不在本文討論範圍內。又本案事務所負責人「雇主」並非指導律師,而是由事務所內其他資深受僱律師擔任指導律師一節,並不影響本文之分析。
貳、勞動法「解僱」議題簡析
一、終止時間點。
女律師自述被「fire」(fire此一英文字以下均稱中文:解僱)是在她「實習那年」,但不確定終止契約關係的確切時間點是在五個月事務所「實務訓練期間」內,或是「實務訓練期間」屆滿但未被事務所留用為正式受僱律師,當然也可能是「實務訓練期間」屆滿已被留用為正式受僱律師後再被解僱。以下分這三種情形作簡短分析。
(一)、「實務訓練期間內」被解僱。
1.實務訓練期間內契約關係屬性。
依法務部民國102年5月22日法檢字第10204529570號函示意旨:「學習律師於實務訓練期間與指導律師間之關係,定位為非僱傭關係,惟學習律師與指導律師於實務訓練期間是否有僱傭關係,仍應依訓練內容及方式,依個案事實認定之。」一般而言,學習律師於事務所實務訓練期間多「邊做邊學、邊學邊做」,也做也學,不能排除有提供勞務的事實,因此宜將之定位為有勞雇關係。
2.事務所實務訓練期間法定為五個月,所以學習律師與雇主間應屬「以受訓或服役等特定目的所成立的特定性定期勞動契約關係。」假如雇主與指導律師為同一人,則同時存在受訓、指導關係與勞動契約關係;倘雇主與指導律師非屬同一,學習律師與指導律師間僅存在受訓、指導關係,但學習律師與雇主間則仍係成立前述特定性定期勞動契約關係。
3.依「律師職前訓練規則」第11條第1項規定:「學習律師於實務訓練期間遇有指導律師不能繼續指導訓練情事者,得陳報受委任(託)辦理本訓練之司法官學院或全聯會准其更換指導律師。」這是學習律師主動陳報更換指導律師,換言之,發動終止契約的一方是學習律師。這與女律師自述是被解僱、是被動終止契約關係者不同,因此應非本條款之情形。
4.再依「律師職前訓練規則」第11條第2項規定:「學習律師不當拒絕指導律師之指導,致影響學習成效時,指導律師得報請受委任(託)辦理本訓練之司法官學院或全聯會處理。」網紅律師的事務所如果是在「實務訓練期間內」援引本條項規定報請全律會(律師研習所)同意後將女律師退訓,雖非全無可能,但如此一來,事情曝光可能對事務所不利,本文判斷此一情事微乎其微。更何況該女律師於2023年底取得執業律師資格,應可推斷已學習期滿及格。
(二)、「實務訓練期間」屆滿未被留任。
1.學習律師在事務所五個月實務訓練期間屆滿,被事務所留用成為正式受僱律師者,固非罕見,但查法律上並無強制締約規定(註二),學習律師並無要求指導律師事務所繼續僱用之權利,但也無必須接受指導律師事務所留用為受僱律師之義務,反之亦然。
2.實務上雖曾聽聞有指導律師與學習律師達成君子協議,要求學習期滿應至少受僱一段期間才可離職之事例者,但此究非法律上義務,假如學習律師不肯續留,淺見以為學習律師應無違約責任。
3.本案在此要討論的是女律師學習期滿如因懷孕(且不肯人工流產)而不被留用為受僱律師者,是否為所謂的「解僱」?查解僱是勞動契約終止的原因之一,既曰「終止」必以先已成立勞動契約關係為前提,假如勞動契約尚未成立,並無所謂「解僱」之問題。
4.如前所述,實務訓練學習期滿學習律師並無權利要求指導律師事務所非留用不可,是事務所未予「留用」為受僱律師,並非勞動法上之解僱。(註三)
5.惟學習期滿未獲留用,確屬「短期失業」,依就業保險法第11條第2項規定:「被保險人因定期契約屆滿離職,逾一個月未能就業,且離職前一年內,契約期間合計滿六個月以上者,視為非自願離職,並準用前項之規定。」
6.學習期滿未獲留用成為正式受僱律師,依本文淺見固已符合「因定期契約屆滿離職」之要件,但因就業保險法第11條第2項另又規定被保險人(勞工)必須離職前一年內「契約期間合計滿六個月以上」之要件,而學習律師在事務所實務訓練期間僅五個月,一般而言不太可能符合這個申領失業保險給付的要件。
7.本件案例據女律師自述其有申領得失業保險給付,因此幾可判斷應非實務訓練期間屆滿未被留用為正式受僱律師之情形。
(三)正式受僱後被解僱。
綜合以上情事,本文判斷本案應該是在實務訓練期間屆滿,雙方合意留用轉為正式受僱律師後再被解僱的可能性最大。此時,涉及的是勞動契約終止合法與否,即解僱有效、無效之問題。
二、解僱原因。
女律師僅自述被解僱,並未交代雇主是以勞動基準法第11條之資遣解僱(俗稱:資遣)或第12條之懲戒解僱(俗稱:開除)來終止勞動契約。但從女律師自述「找不到工作,領失業保險給付」的文句,應可判斷雇主是以勞動基準法第11條之資遣解僱來終止勞動契約,並發給女律師「非自願離職證明」,女律師才能依前述就業保險法第11條規定申領失業保險給付。
三、解僱合法性。
1.女律師自述:「因為(懷孕且)不拿掉小孩被雇主解僱」,這涉及的是解僱合法性問題,其實也不必引經據典,單用常識即可判斷這一定是違法解僱。至於上述雇主形式上可能是以勞動基準法第11條之事由來資遣女律師,不論是援用哪一款,都無解於歧視懷孕解僱而屬違法解僱之事實。
2.更具體的法條是性別工作平等法第11條第2項規定:「工作規則、勞動契約或團體協約,不得規定或事先約定受僱者有結婚、懷孕、分娩或育兒之情事時,應行離職或留職停薪;亦不得以其為解僱之理由。」違反之者,依第11條第3項明文規定:「違反前二項規定者,其規定或約定無效;勞動契約之終止不生效力。」條文後段所謂「勞動契約之終止不生效力」就是解僱無效。
3.除解僱無效的法律效果外,另依性別工作平等法第26條、第29條前段規定,雇主並應對懷孕女工負財產上損害賠償與非財產上損害賠償之賠償責任。
4.行政法上受害女工並得依性別工作平等法第34條第1項規定,逕向地方主管機關提起申訴。地方主管機關查證確認雇主確實違反「第十一條第一項、第二項規定者」,得依性別工作平等法第38條之1第1項規定處雇主新臺幣三十萬元以上一百五十萬元以下罰鍰。
四、結論。
1.本件案例依女律師自述:「因為(懷孕且)不拿掉小孩被雇主解僱」,依性別工作平等法第11條第3項後段規定,雇主之解僱為無效。
2.法律救濟途徑除行政申訴外,民事訴訟程序和一般的違法解僱訴訟並無不同。本案訴訟方面勞工通常請求確認僱傭關係繼續存在、請求繼續給付工資(但應先有準備給付勞務之通知)、請求按月繼續提繳新制勞工退休金等。本案因另涉有懷孕歧視解僱,實務上勞工多會併請求給付慰撫金。
3.保全程序方面,依勞動事件法第49條第1項規定,一有本案訴訟繫屬,法院「得依勞工之聲請,為繼續僱用及給付工資之定暫時狀態處分。」原則上只要「雇主繼續僱用非顯有重大困難者」,法院照准的機率頗高。
4.可能會有爭議的是現在離當初女律師被解僱應該已有一兩年之久,且女律師後來已另行就業,雇主在訴訟中可能抗辯稱:時隔一、兩年勞工對終止契約一節從無爭執,連去勞工局申請調解都沒有,雇主早已信賴勞工不會再起爭執,現驟然起訴有失誠信,且勞工早已另就他職根本無復職意願,亦即提出權利失效等等的抗辯。這些議題勞動法文獻汗牛充棟,作者也曾有多篇文章分析,於茲不贅。
5.以上僅就所涉勞動法「解僱」議題作簡短分析。
註解:
註二、類似的案例可參替代役期滿役男要求用人單位繼續僱用案,臺灣士林地方法院112勞訴81判決、臺灣高等法院113勞上60判決。
2025.5.30補註
頃閱讀本文所述實習律師的「雇主」,於臉書2025.5.30最新貼文表示:「在她確定要生下來以後,她決定主動離開公司」(作者按:該貼文已被臉書系統刪除)。依雇主的敘述,則勞工是主動離職,也就是勞基法第15條自請辭職的意思。勞雇雙方對於離職的原因各執一詞,孰是孰非本來就不是本文關切的重點,本文一開始就已說明是根據女律師「自述」的內容來作勞動法解僱議題分析,事實真相如何並不影響本文的分析。
但雇主2025.5.30的發文則帶來另一個勞動法疑義。女律師自述被解僱找不到工作,有去申領失業保險給付,本文前已說明勞工要去申領失業保險給付,原則上應該憑據雇主發給的「非自願離職證明」。依據女律師自述她有去申領失業保險給付,本文假設通常之狀況,即雇主有發給「非自願離職證明」,但根據雇主2025.5.30的發文,勞工明明是「主動離職」(自請辭職),並不是「非自願離職」,依法雇主不可開立不實的「非自願離職證明」。
假如雇主明明知道勞工是主動自請辭職並非被資遣,但為了協助勞工去請領失業保險給付,從而發給勞工不實的非自願離職證明者,因此需承擔的法律責任,有民、刑事、行政法責任等各方面責任,網路上有大量的資料垂手可得,拙著「勞動訴訟實務」(二版)第475-476頁對此亦有簡略論述,於茲不贅。本件所述兩造都是律師,尤其雇主方面有多年執業經驗,卻對勞動法問題這麼輕忽,實在令人遺憾。
作者按:
因網紅律師該篇原始貼文已被臉書系統刪除,爰謹提供該段敘述勞工係主動離職的擷圖連結替代。
2025.10.1第二次補述
根據2025.10.1知新聞網路新聞的報導,該被害女律師向台北市勞動局申訴雇主「懷孕歧視」,並向法院提告求償100萬元。台北市勞動局性別平等工作會日前審定該事務所構成懷孕歧視,將開罰30至150萬元,並公布雇主姓名,求償案將於本周四(2日)於台北地院調解。另外,(事務所負責人)呂OO今年5月間在臉書公布林女姓名、職業、肖像甚至性生活隱私,林女昨(30日)向新北地檢署控告呂OO觸犯《個資法》、強制罪2罪,另向台北律師公會申訴呂男以工作要脅逼墮胎,違反律師倫理,應送懲戒。
謹此補述。